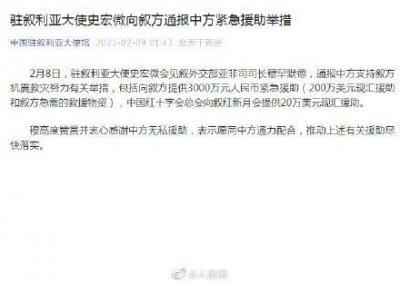读懂论语:(2.12)子曰:“君子不器”

2.12子曰:“君子不器。”
《论语》之“学”强调做人,通过“学”成就“君子”,是为“学”的第一步,在“君子”的基础上再成为“圣人”,是为“学”的终极目标。“君子”作为儒家“好学”之人的代名词,对其内涵亦有不同理解。本章及以下两章,就是集中辨析“君子”这一概念,为“好学”者成就真正“君子”提供指导。
“君子不器”
《论语》第一篇多次涉及“君子”这一概念,并指出过其涵盖范围很广,从一般“好学”者到“有道”之人都可以称为“君子”。那么,从一般“好学”者到“有道”之人,有没有一个共同特点或属性?有。孔子说的“君子不器”,就是所有可称之“君子”之人的共同特点和属性,也就是“君子”的形象与人格。
“器”,指器物的总称。器物是有专用的,不同的器物有不同的用途。“君子不器”字面意思就是“君子不能象器物一样”。之所以指出“君子”应该“不器”,就是因为很多人把“君子”看作了“器”,误解了儒学对“君子”的定位。
“圣人”相对于“君子”而言,更具有理想形象与人格,“圣人”的形象与人格是什么?以前论述过,“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从心所欲不踰矩”,此即“圣人无人心”,也就是说,“圣人”就是彻底了知世间一切的人,从没有固执的己见和自以为是,而又能随顺一切人情世故,在一般人看来,就如同“愚人”。“圣人”当然不是“愚人”,但也不是其他人,除了“圣人”之名,“圣人”其实已经失去了一切作为人的“人格”,但又不失所有的“人格”形象,如果再勉强定义其“人格”,也只可以“神格”命名。一个具有“神格”的人,再认定其为什么“人格”的人已经多余,等于无中生有。即使“圣人”这一名称,也是对这一“神格”的变相称谓,只是一个权宜符号,根本就不存在“圣人”这一固定类型的人,若一定称某种形象或类型的人为“圣人”,那一定不是“真圣人”。“圣人”就是没有任何固定形象标准的人,加任何定义甚至符号或标签都是多余。形象即“相”。《金钢经》中说:“不住于相”,“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就是没有形象概念的意思。“圣人”的这种“不相”,就可以称之为“不器”。
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就是以“形象”来区别“道”与“器”。“道”是形象背后看不见的那个“力量”,当“道”起作用的时候,必然体现在形象上,但形象不是“道”;“器”是形象前面看得见的那些物体,物体是形象存在的保证,有物体才有形象,但物体不等同于形象,同一个形象可能由不同物体构成。不同物体具有不同属性,也有不同用途。人也同样是物体,亦即“器”。作为一般人,有“人”的形象,就有“人”的用途。当一个人被称为什么“人”时,其实就是在以什么器被使用。一个“孝”的人,就是一个用“孝”之器,一个“忠”的人,就是一个用“忠”之器,一个“信”的人,就是用“信”之器,一个“仁”的人,就是一个用“仁”之器,一个“圣”的人,就是用“圣”之器。如果真有“圣”这一种人,则“圣人即器”。
在一般人心中,其实是存在这一“圣人”形象的,由这一形象,而推定存在“圣人”这一种人,即“圣人”之器。由此可见,所谓“圣人”,这只不过是一般人对“圣人”贴上的标签,在一般人心中“圣人”是器。而真正的“圣人”,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圣人”,当然,也不是其他任何概念的“人”。也就是说,在“圣人”心中,自己不是任何物体,也不是任何物体指代的形象,故说“圣人不器”,这是“圣人”的自我认识,也是真正的见解,是正确的看法。而“圣人是器”则是一般人的认知,是不正确看法。
“君子不器”是孔子对“君子”的期望,是对“君子”理想形象与人格的定位,更是为所有“君子”从事道德修养(即“学”)而制定的一个行为原则。在一般人心中,“君子”确实是器。“君子”可以是一个政府官员,则“官员”就是被用之器;“君子”可以是一个将军,则“将军”就是被用之器;“君子”可以是一个农民,则“农民”就是被用之器。“君子”可以是任何形象之人,则任何形象都是被用之器。其实,无论“君子”还是“小人”,都是以器而生活在世间,并以一定的用途(角色)被摆放于所在的位置上,这就是世间“现实”,也是人类社会得以正常运转的基础。
对人类社会这种“现实”的认同,恰恰是人类身心不能自由的原因。所谓“圣人”,就是看透这种“现实”的人。看透“现实”并不一定要逃避“现实”,所以“圣人”仍可以生活在人间。“圣人”是“君子”的理想,作为“君子”,在个人修养中当然要效法“圣人”的行为,“圣人不器”,作为“君子”,也应当做到“君子不器”。
“君子不器”是“君子”的自我认知,作为“君子”,在一般人看来,不可能做到“不器”,即使“圣人”也一样,总要在社会上扮演一定角色。孔子办学,自然是弟子们的老师,没有哪一个弟子会否认孔子“老师”的身份,孔子表面上自然也会随顺弟子们的称呼,但其内心绝不会认为自己就是个老师,也绝不会认为自己作为老师应该怎么怎么样。孔子作为老师的一切行为,都是在回应弟子们“学道”的要求,而其内心并没有一般人的自以为是。这就是圣人内心“无”而外表“有”的形象。作为君子,在社会上扮演一定角色也是必然的,被别人视作“器”也是必然的,这里的关键在于君子自己怎么看待自己,如果自己也认为自己是“器”,内心摆脱不掉所扮演的角色,并且坚持认为应该怎么样,那就是“住于相”,有了“我相、人相”。角色为“名”,怎么样为“相”,这种固执于“名相”的认知,就是阻碍“君子”见道、得道的根本原因。作为以“学道”为己任的“君子”,摆脱世间“名相”对心灵的束缚是一项实实在在的修养功夫,不执着于“名相”,就是不执着于作“器”,不役于物而超然世外,这才是真正的“学”,这才是正确的道德修养。故曰:“君子不器”。
这是孔子为“君子”的理想人格所作的定义,亦是“君子”为学之“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