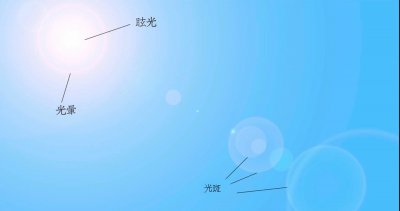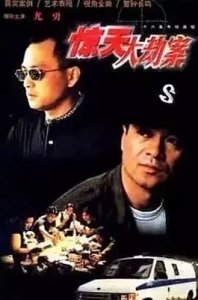89年17岁日本高中生失踪,父母苦寻无果,警察找到时她已成1块水泥
日本警察走进江东区的一家工厂,在角落里,他们找到了一个灌满水泥的汽油桶,其中一个警察颤抖着说:“是顺子,顺子就在里面。”
1988年11月至1989年1月,在日本东京都足立区绫濑发生了一起绑票禁锢,侵犯谋杀和弃尸的严重罪案,此案被称为日本女高中生油桶装入杀人事件。
案件在日本影响极大,被多次改编成影视和动漫。这起案件还有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绫濑水泥案。
噩梦的开端
古田顺子,生于1971年1月18日,崎玉县人,就读于崎玉八潮南高中。
古田在学校是有名的品学兼优生,长相可爱且接物待人均十分亲切,由于家境一般,古田从很早便开始准备就业,也拿到了一所家电卖厂的录用通知,一毕业便能直接入社工作。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对人生有着清晰规划,努力上进的花季少女,却不幸成为本案的受害者,难以想象她到底经历了怎样的非人折磨。
而最令人出其愤怒和惊愕的是,这起案件的作案者不是成年人,而是四名与古田年纪相仿的不良少年。
主犯宫野裕史,1970年4月30日生。家庭条件优越,因家庭疏于照顾,从而放纵了其恶劣霸道的性格。
从学校退学后,在家附近聚集了一帮闲散青年,结交成立了一个名为“极青会”的团体。
第二主犯神作让,1971年5月11日生,典型的不良少年,与宫野认识并混在一起后,性格越加恶劣。
从犯凑伸治,父母感情不合,家中时常发生口角。他在压抑的家庭环境中逐渐崇尚用暴力发泄情绪和解决问题,自愿加入“极青会”。
从犯渡边恭史,因家庭离异,性格阴暗。巧合下认识了宫野的姐姐,为追求其姐姐而成为宫野的小弟。
1989年11月25日晚上6点,宫野突然找到凑伸治,要凑伸治跟他一块去街上抢包。凑伸治马上从朋友那里借来一辆摩托,两人开着车驶向夜幕初降的街道。
到了晚上8点半左右,他们发现了骑着自行车,正从打工地往家里走的古田顺子。
宫野和凑伸治一个扮作黑社会,一个扮作好心人,演戏哄骗古田上了宫野的车,之后宫野侵犯了古田。
事后,宫野便给先前回家的凑伸治打电话,让他开车来接自己,正巧神作让和渡边恭史也在。于是三人马上出门,开着丰田找到了宫野,并用车将古田顺子劫持到了凑伸治的家中。
从进入凑家的这一刻起,古田顺子依旧幻想着这群凶恶的不良少年能够尽快放了她,然而她终究没能活着走出这所房子。
宫野一伙将古田劫持到凑家二楼,这里是他们长久以来建立的所谓“基地”。
因凑家父母对次子凑伸治失望至极,加上又畏惧他的小团体,所以重心全放在用功读书的长子身上,对他们团体的事基本不想干涉也不敢过问,而这也间接造成了古田的悲剧。
古田被劫持回凑家的这天,正好凑伸治的父亲在参加单位的团建活动,家中只有凑伸治的母亲和哥哥在家。
这伙人大半夜吵吵闹闹地将人带回家的时候,其实已经吵醒了凑伸治的母亲,但因为害怕他们,也没有多问。
对于宫野一伙在家中的胡作非为,凑伸治的家人向来都是眼不见心不烦的态度。
所以在后期即使他们已经知道家中囚禁了一个女孩,出于保全自身和家族颜面的心理,谁也没有向古田顺子伸出援手,而是选择了像鸵鸟一样逃避。
被囚禁的41天
11月28日晚上6点左右,古田顺子被劫持囚禁的第三天。
宫野已经按捺不住显摆自己能耐,便以头目身份给极青会的四个未成年手下打电话,以“看点好东西”为由要他们到凑伸治的家中集合。
四人到后,宫野得意地向他们展示了被囚禁整整三天的古田。随后几人开始喝酒吹嘘,直到时间越来越晚,这时感到有些乏味的宫野想寻求刺激,竟提出众人一起侵犯古田,
11月30日,凑伸治的母亲到二楼来收拾房间,看见了被囚禁在屋里的古田,她其实已经知道自己儿子那伙人带回来了一个女孩,只是没想到会囚禁在自己家。
而同为女性的这位母亲看着遍体鳞伤的古田,只是轻飘飘地丢了句让她赶紧回家的话,之后便收拾东西下楼了。
在之后的日子里,古田遭受了惨无人道的虐待,这群少年不断地以她的身体取乐,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她的痛苦之上。
渐渐地,古田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囚禁她的房间也变得恶臭起来,这个时候宫野一行人意识到,眼下既不能放走她,留下她又可能随时都会死。
但对于宫野这群缺乏责任感的未成年人而言,古田顺子只是一个用来取乐和消遣的玩具,在如何对待她的这个问题上,他们的决定其实显而易见:那就是让她死。
1989年1月4日凌晨6点半,古田顺子被囚禁的第41天,她遭受了最后一场殴打,而顺子也在这场殴打中断了气——她终于得到了解脱。
与此同时,古田顺子的父母正在苦苦寻找她,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女儿已经去世了。
几名少年在桑拿房待了整整一天,第二天凌晨,也就是1989年1月5日,几人回到家中,意识到古田已经死亡。
但他们此时却没有半点罪恶感,只是纠结该如何处置古田尸体。最后选择用毛毯和旅行袋将她的尸体草草地裹了一下,抬下楼装进车的后备箱中。
又把车开到了邻近工厂的一处空地上。四人将工厂里的汽油罐搬了过来,把古田顺子的尸体连同旅行袋一起丢到了油罐中,并倒入水泥。
当天上午8点,原本计划将这个汽油桶扔到海里的宫野一伙将车开到江东区的海边工地上。
然而这时他们却害怕起来,担心被人发现自己的可疑行踪,便将这个汽油桶丢弃在工地的一个不起眼角落里,之后便开着车扬长而去。
回去后,少年们彻底清理了汽车后备箱,并将二层所有古田用过的物品统统打包装进车里,开车带到海边全部烧掉。
罪恶暴露
1989年1月23日,古田被害后的第18天。
足立区绫濑警署将宫野和神作两人带回警局,起初两人还以为是古田的事暴露了,但在警察的讯问中才得知,自己是因为去年十二月在酒店侵犯一个陪酒女郎,对方报了警。
于是两人放下心来,大胆承认了此事,但不承认胁迫对方。
于是警方申请了搜查令,去往两人家中对其私人物品进行搜查,以找到能证实两人所说从未胁迫对方的证据。
在此期间,宫野和神作因承认陪酒女的事情,但因侵犯事实尚且不清,被关押在少年看守所内等待警察搜查出证据。
1989年3月29日,两名检察官来到东京都练马区少年犯看守所内,分别面见了宫野和神作。
在面对宫野时,检查官拿出了一条在他家搜查出来的女性内裤,见宫野的目光似有慌张躲闪。
老练的检察官意识到事情可能并非只是侵犯那样简单,于是他半信半疑地诈问:“你杀了人吧?”
而宫野自从被关进看守所以来,每日每夜都被幻听和幻视所折磨。
之前在把古田尸体装进汽油桶后,因宫野曾多次听古田说想看她先前一直追的剧,还买来该剧最后一集放入汽油桶内,以求古田不会化作厉鬼来找他。
看守也多次反映宫野一到夜里便在牢房里大喊大叫。他的精神实际早已崩溃,加上检察官拿出这件似是而非的“证据”,心理防线便不攻自破,轻易地承认了杀人事实。
检察官也没想到自己的一句诈话会牵扯出一桩杀人案,于是他步步紧逼,逐渐套出古田顺子被监禁侮辱杀害到抛尸的整个事件过程。
几天后,包括渡边,神作,凑伸治以及参与侵犯古田的总共六名少年全部被拘捕到案。
警察找到顺子的时候,她被埋在水泥里,和这块水泥融为一体。
紧接着法医对可怜的顺子进行尸检,发现她竟然怀孕了,然而这个孩子和顺子一样,死在不见天日的、灌满了水泥的汽油桶里。
这个案子震惊了全日本,甚至还让日本修改了少年法,但令人遗憾的是,施暴的恶魔们,没有一个被判处死刑。
1989年7月31日,东京地方法庭对宫野,神作,凑和渡边四人进行了开庭审判。
大约一年后,宫野,神作,凑伸治,渡边四人分别被判处17年有期徒刑,5-10年不定期徒刑,4-6年不定期徒刑,和3-4年不定期徒刑。
如今,他们已经全部出狱。
令人发抖的犯罪心理
回顾本案其实不难发现,涉案的犯罪少年均是原生家庭有问题,但是当我们深究其原生家庭时,又会发现,这些少年的父母并无一人涉及犯罪,甚至连违法行为都没有。
如果一个行为人,在父母双方或者双方有越轨行为的家庭环境下成长,那么这个行为人极有可能成长为易感体质,即后续犯罪的可能性会很高。
像这种没有越轨行为的家庭环境,对行为人行为和心理的关注则应当转移到学校和朋友团体中。
虽然此案中行为人退学或休学可能是因为其行为对学校其他学生造成了威胁,但是在价值观尚未树立,该受到的教育的时候脱离学校,是一种非常强的负面反馈。
因为学校除了教育,也具有约束和保护作用,即行为人依旧是受教育的学生,而非无管制的社会人。
退学和休学使行为人失去了这种保护,加深了行为人内心的自我否定,使其更加不受约束。
而朋友团队的助推表现在于,这个案子除了宫野一开始对古田的侵犯,其余犯罪行为均是不少于两人的群体行为。
因行为人属于关系亲密的朋友,他们的行为都是互相影响的,每一次犯罪行为的发生都是一种负面反馈的交流,因为同一件事,大家都在做,所以不存在有人被排斥。
也因为大家都在做同一件事,大家都在做,如果不做一定会被排斥。这便是群体犯罪心理。
当个体融入群体时,个体的自我意识,自我控制以及自我评价都会下降,个体自我意识水平降低的时候,个体的侵犯性就会增加,这也是本案中持续侵犯性行为不断发生的原因。
另外则是群体缺乏对行为后果的认知,就是说此案中的群体犯罪行为,因为犯罪主体被捆绑在一起,也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当他们以群体行动时,个体的责任意识其实是分散或者根本没有的,因为每个人都觉得其他人会有分寸,会把握好那个度,所以他们直到后期才察觉到会发生不好的后果。
实际上只要有一人醒悟收手,带来的正面反馈就会抑制侵犯行为,可惜的是这个群体全程表现出的都是严重的侵犯行为。
另外就是作为团队领导者的宫野,他属于原发型犯罪者,这种类型的犯罪者属于最难改变的一类。
犯罪者从少年时期开始,通过不良交往和违法行为的尝试,慢慢积累经验,逐步发展成为个性化的犯罪心理,并开始实施犯罪行为。
这类犯罪者的社会化过程不完全,或是经历了错误的社会化,第一次犯罪年龄早,且容易根深蒂固。
宫野在退学后进入社会,对于越轨行为群体是不抗拒的。那时他加入了暴走族,而日本当时的暴走族属于黑社会的前置阶段。
因而宫野开始正式地接触犯罪,犯罪心理也开始了快速个性化和动力定型的转变过程,在此过程中,宫野的犯罪技能也逐渐趋于完善。
这个犯罪心理的转型过程同样可以套用在凑伸治,神作以及渡边身上,但原发型的犯罪者很难得到矫正,所以他们再犯的可能性非常高。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中的几个行为人不存在显性的人格障碍,多数行为是因为群体影响和青少年时期的认知错误造成的。
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在抛尸路上的恐惧心理,这是犯罪行为实施完成后,犯罪心理进入到后续潜伏阶段的正常反应。在这时,行为人开始受到各种负面心理的攻击,恐惧便是其中之一。
再以案件的旁观者——凑伸治一家的角度来看。他们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到犯罪,但实际是助长了犯罪行为。
只是这就好比“扶不扶”的问题,只能从道德的角度谴责,而不能要求法律惩罚。这里面最明显的就是凑伸治的母亲,在已知晓古田被囚禁在自家二楼时,仍然采取漠视的态度。
这其实和凑伸治对待她的态度有关。凑母虽然看上去为人谨慎,但她曾多次遭受凑伸治的殴打。
身为一名母亲,这是极大的耻辱,因而凑母这种假装看不见恶行的行为,并非是因为她缺乏良知——而是由于羞耻心和自尊心,让凑母不愿意承认自己养出了这样为非作歹,殴打母亲的儿子。
而对凑伸治而言,他虽然生活在这个家里,但与他有血缘关系的三个人都已经主动或被迫无视他的存在。
因此他为了找寻归属感,必然会需要一个群体对他的容纳,这便是他加入“极青会”的原因。他带着自己的小团体在家里为所欲为,也是一种出于对家人忽视自己的报复和宣泄。
诚然,凑伸治父母及其兄长,的确漠视了犯罪,间接推动了悲剧发生。
“大义灭亲”人人都能说,但事实就是人们往往会在自己至亲出现犯罪行为时,选择无视甚至包庇这些罪行。
除了血缘亲情的原因外,因为人是社会性动物,当家族出现污点时,会导致这个家族在社会上为人所诟病,所以“觉得羞耻”。
于是便假装没听见或没看见,兴许就是这些犯人家属的心态。
当然,这并不是要试着去体谅他们的意思,只是要以此为戒,毕竟装聋作哑不会让事情变好,也不能够让自己免于良心的责罚。
此案中,对四名行为人的判决也值得深思,为本着拯救和教育青少年的目的而依法进行从轻判决,与成人犯罪的刑罚相比,属实显得有些宽宏大量。
但本案中的四名少年均是再犯可能极高的原发型犯罪者,而宫野和凑伸治刑满释放后,也的确再次表现出了社会危害性。
实际上,四人在犯罪时对自己的行为均有清醒的认识,知道自己会对受害者造成可能死亡的后果,只是他们放纵了这个结果发生。
并且在审判时,未成年人这个身份也成为了他们的免死金牌。这对于本难矫正的原发型犯罪者而言,无疑是一份极大的甜头。
但总体而言,未成年人的量刑仍旧需要结合案情综合考量,不能以偏概全,也不能彻头彻尾保护。而这也会是一条全社会上下而求索的漫漫长路。
-完-
编辑|书书